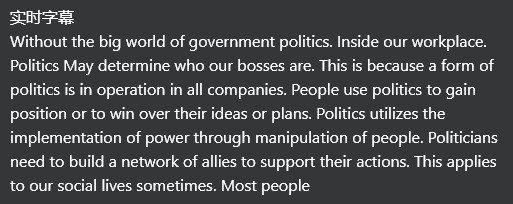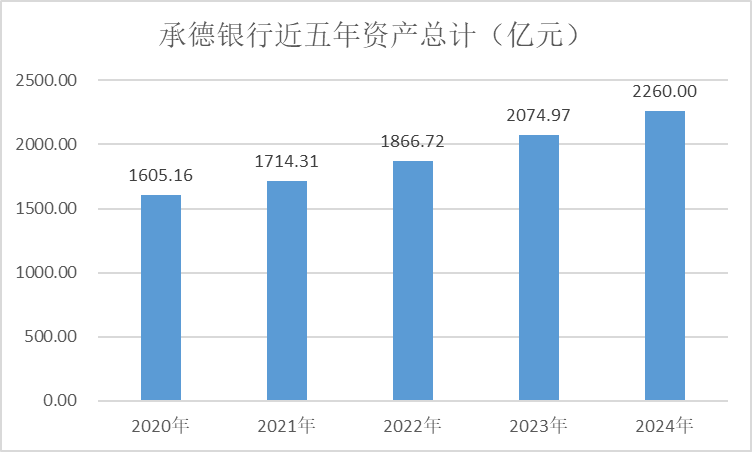声场,作为由人声、音乐与环境音共同构筑的叙事场域,在《好东西》中不仅是氛围的烘托,更成为权力关系与情感暗流的隐喻载体。影片以单亲母亲王铁梅、独立女性小叶与小女孩茉莉为核心,通过日常片段展开三人的成长叙事。作为近年来华语女性主义影像转向的代表作,影片超越“女性与规训”的传统命题,转而聚焦觉醒之后女性所面临的现实摩擦,探讨她们如何在制度化话语与日常生活的夹缝中,通过聆听与发声,走向一种兼具锋利与温度的自洽。这一以“聆听—回应”为动力的叙事机制,为中国语境下的女性表达注入了独特的情感深度与文化厚度。,![图片[1]-新大众影评 | 聆听之下:《好东西》声场隐喻中的主体觉醒与自洽-上淘有品虚拟资源下载](https://ent.ycwb.com/pic/2025-12/01/53825614_04e9ce5a-858c-462b-b454-0f4b8c97e201copy.jpg) ,声场隐喻的叙事建构,影片以声场作为结构性隐喻,构建出家庭与社交两类声学空间,分别指向女性在不同场域中的权力处境与情感状态。家庭作为私密声场,承载着女性劳动的隐形性与情感的压抑性;社交空间则外化了制度化话语对个体声音的遮蔽与规训。这一设计巧妙绕开了视觉中心主义对女性形象的固化凝视,使声音成为解读性别权力结构的关键符码。,在家庭这一女性主体意识初萌的声场中,王铁梅与茉莉构成了一个看似女性主导、实则暗含传统束缚的单元。铁梅承担全部家务,茉莉在母职凝视下成长,二人的声音在家庭频谱中既相互依存又彼此角力。影片以极具原创性的“声音游戏”段落,揭示家庭劳动的隐形化制——茉莉将煎蛋声听作暴雨、吸尘器声幻化为龙卷风,这种诗意的听觉转换,实则是将女性日常劳动自然化、从而被视作“理所当然”的隐喻。声音在此成为可感的权力载体,为后续女性的觉醒埋下伏笔。,相较于家庭的隐性控制,社交场域的声学秩序更为外显与制度化。键盘声、对话与笑声交织成一套强弱分明的规则体系,个体经验的微弱频段常被更高的音量所覆盖。铁梅发表单亲母亲自述后遭遇的网络暴力,正是制度化话语压制个体发声的典型体现。诸如“卖惨博流量”“不负责任”等批判,本质是固化性别叙事对女性经验的否定与消音。,
,声场隐喻的叙事建构,影片以声场作为结构性隐喻,构建出家庭与社交两类声学空间,分别指向女性在不同场域中的权力处境与情感状态。家庭作为私密声场,承载着女性劳动的隐形性与情感的压抑性;社交空间则外化了制度化话语对个体声音的遮蔽与规训。这一设计巧妙绕开了视觉中心主义对女性形象的固化凝视,使声音成为解读性别权力结构的关键符码。,在家庭这一女性主体意识初萌的声场中,王铁梅与茉莉构成了一个看似女性主导、实则暗含传统束缚的单元。铁梅承担全部家务,茉莉在母职凝视下成长,二人的声音在家庭频谱中既相互依存又彼此角力。影片以极具原创性的“声音游戏”段落,揭示家庭劳动的隐形化制——茉莉将煎蛋声听作暴雨、吸尘器声幻化为龙卷风,这种诗意的听觉转换,实则是将女性日常劳动自然化、从而被视作“理所当然”的隐喻。声音在此成为可感的权力载体,为后续女性的觉醒埋下伏笔。,相较于家庭的隐性控制,社交场域的声学秩序更为外显与制度化。键盘声、对话与笑声交织成一套强弱分明的规则体系,个体经验的微弱频段常被更高的音量所覆盖。铁梅发表单亲母亲自述后遭遇的网络暴力,正是制度化话语压制个体发声的典型体现。诸如“卖惨博流量”“不负责任”等批判,本质是固化性别叙事对女性经验的否定与消音。,![图片[1]-新大众影评 | 聆听之下:《好东西》声场隐喻中的主体觉醒与自洽-上淘有品虚拟资源下载](https://ent.ycwb.com/pic/2025-12/01/53825614_22277094-fb28-4dce-b548-ceaaec1cd766copy.jpg) ,声场中的主体觉醒与自洽,聆听,成为女性在复杂声场中重建自我的起点。小叶的倾听源于其成长过程中对情感的敏锐感知——她能捕捉铁梅叹息中的疲惫与茉莉沉默中的求助。铁梅则从选择性静默走向开放接纳,她最初屏蔽外界刻板噪音,专注经营与女儿的小世界;随着与小叶、女儿的互动深入,她逐渐听见并接纳自身与他人的真实感受,最终卸下“完美母亲”的盔甲,在承认脆弱中重塑身份边界。,发声,是内在意识转化为外在实践的关键一步。茉莉的三篇作文清晰地勾勒出其主体意识的成长轨迹:从最初的《我不再幻想》到后期明确表达喜好与思考,她的书写逐渐褪去自我规训,展露出未被完全驯服的女性本真。在身体层面,小叶通过舞台上的乐器与歌声构筑了一个可被感知的能量场;铁梅则以现实中的直接对话与行动,将抽象的权利诉求具象化。她们共同证明:发声不仅是言语的表达,更是身体的实践与边界的建立。,觉醒与自洽在聆听与发声的往复中逐渐成形。影片从家庭与社会两个维度,呈现了个体觉醒向群体联结的转化。家庭内部,铁梅与茉莉的代际对话从单向教化转向双向聆听;社会层面,女性之间的同温层对话扩展为跨圈层的公共表达。她们在互助中拆除沉默的壁垒,将个体困境转化为可被共同讨论的公共议题,推动性别话语进入更广阔的声场。,结语,《好东西》并未试图为女性生存提供标准答案,而是将思考隐于对聆听方式的探索之中:如何辨别噪声与真实声音,如何将沉默转化为一种权利,如何把发声视为选择而非义务。当觉醒成为一种持续的练习,自洽成为对自我边界的耐心调试,影片便开辟出一条不依赖视觉暴力、不占领道德高地的“第三路径”。它让女性在声场的隐喻中,既保有直面结构的锋利,亦留存修复关系的温度;在“被听见—能聆听—敢沉默”的动态循环中,将更为复杂、也更为真实的女性命题,交还给观众与时间。
,声场中的主体觉醒与自洽,聆听,成为女性在复杂声场中重建自我的起点。小叶的倾听源于其成长过程中对情感的敏锐感知——她能捕捉铁梅叹息中的疲惫与茉莉沉默中的求助。铁梅则从选择性静默走向开放接纳,她最初屏蔽外界刻板噪音,专注经营与女儿的小世界;随着与小叶、女儿的互动深入,她逐渐听见并接纳自身与他人的真实感受,最终卸下“完美母亲”的盔甲,在承认脆弱中重塑身份边界。,发声,是内在意识转化为外在实践的关键一步。茉莉的三篇作文清晰地勾勒出其主体意识的成长轨迹:从最初的《我不再幻想》到后期明确表达喜好与思考,她的书写逐渐褪去自我规训,展露出未被完全驯服的女性本真。在身体层面,小叶通过舞台上的乐器与歌声构筑了一个可被感知的能量场;铁梅则以现实中的直接对话与行动,将抽象的权利诉求具象化。她们共同证明:发声不仅是言语的表达,更是身体的实践与边界的建立。,觉醒与自洽在聆听与发声的往复中逐渐成形。影片从家庭与社会两个维度,呈现了个体觉醒向群体联结的转化。家庭内部,铁梅与茉莉的代际对话从单向教化转向双向聆听;社会层面,女性之间的同温层对话扩展为跨圈层的公共表达。她们在互助中拆除沉默的壁垒,将个体困境转化为可被共同讨论的公共议题,推动性别话语进入更广阔的声场。,结语,《好东西》并未试图为女性生存提供标准答案,而是将思考隐于对聆听方式的探索之中:如何辨别噪声与真实声音,如何将沉默转化为一种权利,如何把发声视为选择而非义务。当觉醒成为一种持续的练习,自洽成为对自我边界的耐心调试,影片便开辟出一条不依赖视觉暴力、不占领道德高地的“第三路径”。它让女性在声场的隐喻中,既保有直面结构的锋利,亦留存修复关系的温度;在“被听见—能聆听—敢沉默”的动态循环中,将更为复杂、也更为真实的女性命题,交还给观众与时间。
(唐晓芳 华南农业大学),声场隐喻的叙事建构
© 版权声明
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,未经允许请勿转载。
THE END
喜欢就支持一下吧